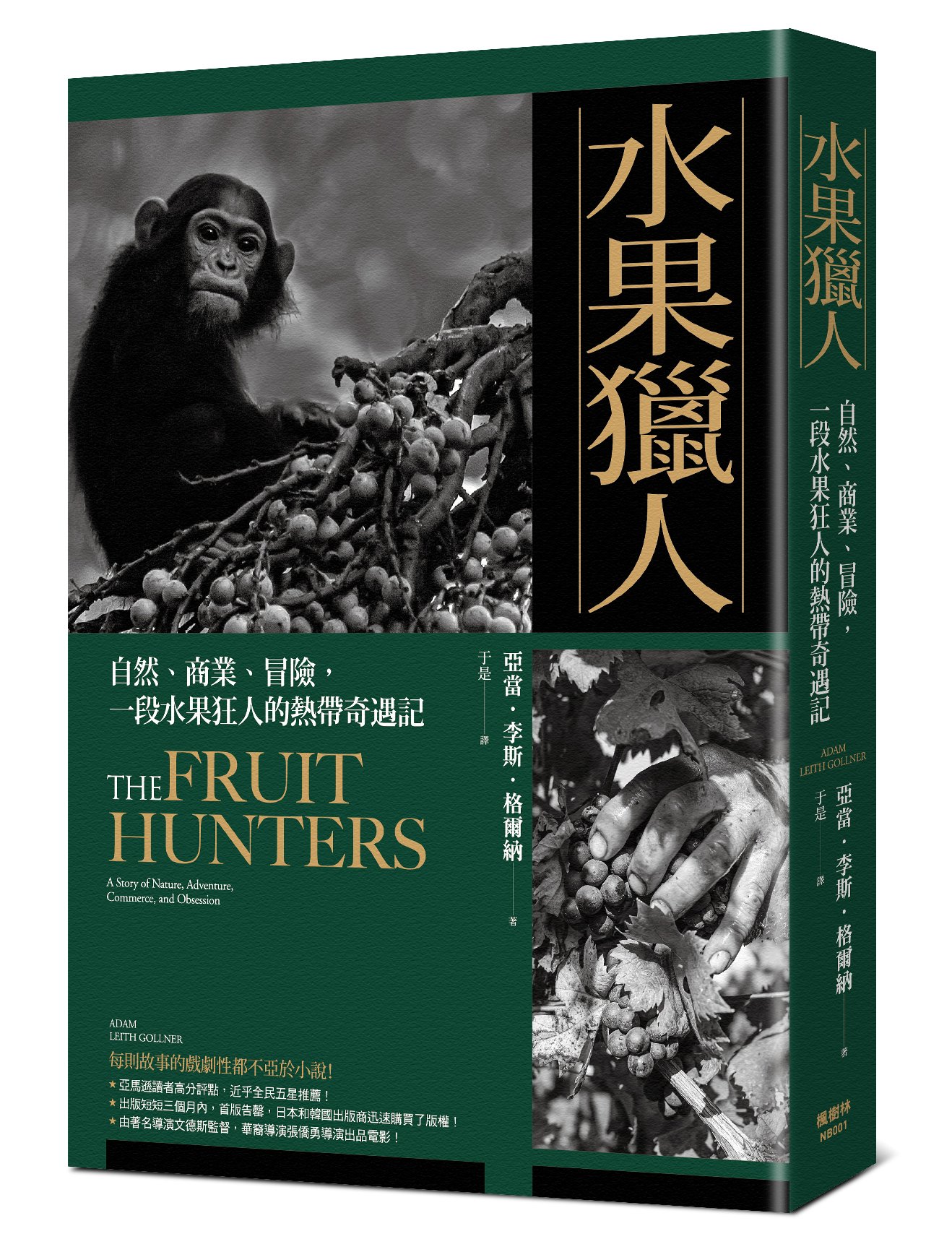果樹,果樹,除了風雨沒人知道你。
你不擔心嗎?你離去時,他們袖手旁觀。
—— 尼克 ‧ 德雷克(Nick Drake),《果樹》
新罕布夏州,窮巷果園。雨後空氣裡充滿著掉落的蘋果,沁人心脾的濃烈酸甜味道。在農場小站裡,在果凍和果醬後面,在一櫃檯未經高溫消毒、禁酒時期早期風格的蘋果酒後面,擺著一堆奇怪的蘋果,標牌上寫著「怪品種」。店主會慫恿路過的人嘗一嘗。
赤褐色粗糙果皮的「阿什米德的果核」(Ashmead’s Kernel)相當古老,可追溯到西元 1700 年,含有獨特的肉豆蔻葡萄酒味。「冬天的白卡爾維爾」(Calville Blanc d’Hiver)像小小的青南瓜,幾瓣兒屁股向外突,是十六世紀烹飪用的蘋果,味道好得沒法形容。湯瑪斯 ‧ 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最愛的蘋果是「埃索普 ‧ 斯皮曾伯格」(Esopus Spitzenberg),我從沒嘗過那麼無與倫比的味道,堪稱登峰造極的蘋果。一口咬下這些蘋果,彷彿立刻穿越到了古代:他們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廷臣、富有的維吉尼亞地主華錦人生的滋味。
窮巷果園的斯蒂芬 ‧ 伍德(Stephen Wood)下巴堅硬方正,自信滿滿,他對這些怪模樣的祖傳果品讚譽有加,他的農場因為他們才得以運營。從 1965 年開始,直至 90 年代初,伍德一直種麥金托什和科特蘭,和所有蘋果種植者一樣,這兩種主流蘋果讓他瀕臨破產。「鑒於我們無法操控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全球性過度栽種蘋果,整個行業都快被榨乾了,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伍德長嘆一聲,讓我想起加里 ‧ 斯奈德曾經說過的話。
等伍德意識到買蘋果比種蘋果便宜多了,他決定試試新招數:祖傳品種。把古品嫁接到他的麥金托什蘋果樹上,他發現有些果子的味道太驚人了。「越難伺候的果子我越喜歡 —— 他們能把你驚得合不攏嘴。」他說,「在這些異類中我們發現了一些品種,能結出驚人高品質的果子。」他專注於十幾種精選品種,繼而著手開拓新市場。把他們裝進漂亮的盒子,然後寄給城裡的高端市場,需求量迅速上漲。他賣出了好多「格萊斯灰蘋果」(Pomme Grise)—— 路易十六偏愛的品種,利潤幾乎是麥金托什的 5 倍。
「這麼做是否英明?尚未有定論。」伍德,這位哈佛大學中世紀歷史專業的高材生繼續說道,「這是很刺激的冒險,但總比坐等一個垂死的產業復活要好。十年之內我會告訴你,這算不算耍小聰明。但這麼做是有希望的,給我們一個機會去種真正特別,說不定再也買不到的東西。」
伍德只是這股潮流中的一員。在滿足於低劣水果的市場裡,小型種植者必須有想像力才能有競爭力,必須出奇制勝,開闢新觀念。那些正在種植稀罕特品並願努力市場化的果農們,漸漸弄明白了:有了這些果子,他們可以漫天要價。
「對農場主來說,可持續性意味著收支平衡。」彭林特品果園的傑夫 ‧ 里格(Jeff Rieger)這麼說,他的果園位於加利福尼亞北部。「具體地說,要賺到足夠的錢繳稅,並能預留第二年的開支。」里格已把注意力完全轉移到祖傳特品中去了:阿肯色黑蘋果(Arkansas Black)、青梅李子(greengage plum)和夏洛特香瓜(Charentais melon)。他還模仿日本古法,做出了乾柿子。把新鮮的柿子暴曬幾周後手工揉捏,直至果肉變成餅泥狀。做好的乾柿子很柔軟,表面還有一層天然的白色粉霜狀果糖。不管是賣給洛杉磯的聖塔莫妮卡農夫市集,還是賣給湯瑪斯 ‧ 凱樂(Thomas Keller)那樣的明星大廚,里格的乾柿子都開價三十三美元一磅。2006 年的所有收成在幾星期內就賣光了。
吉姆 ‧ 邱吉爾(Jim Churchill)和麗薩 ‧ 布倫內斯(Lisa Brenneis)經營著邱吉爾果園。他們自稱「造反牌」,在我嘗過的所有橘子裡,數他們的橘子最棒:嬌小迷人,甜甜酸酸,這種美人橘是日本古品,芳名「紀州」(Kishus)。他們參觀了位於里弗塞德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柑橘品種收藏館之後萌生了此念,種了九百多個栽種品種,包括枳橘(citrangequat)、百佳羅羅(megalolo)、橘柚(orangelo)、橘橙(tangor)、枳檸檬(citremon)、枳橙、枳柚(citrumelo)、橘檸檬(lemandarin)、血酸橙(blood lime)、紫色橘肉的橘柚(tangelo)和果皮黃綠條紋、果肉粉紅的檸檬。「我們去問大學生們吃什麼,因為他們整天都在那些果園裡逛來逛去。」布倫內斯說。同學們一致表態:最愛吃紀州橘。邱吉爾果園的紀州橘大豐收,在加利福尼亞農夫市集裡被搶購一空,還可以郵購。鼎鼎大名的帕尼斯餐廳也有賣,不加什麼廚藝,直接當甜點賣。他們有些果品是真正獨一無二的,比如酸度很低的香草血橙,吃起來竟然有香草霜淇淋的味兒。

我嘗過的最古怪的橘子,是在邱吉爾果園附近的歐佳農場裡。那是一款無名的突變果品,那味道像極了雞湯麵。所有味覺要素全部都有:雞腿肉、雞胸肉、雞湯,甚至包括麵條。但在我看來,沒有別的柑橘比得過邱吉爾果園的紀州橘。好萊塢農夫市集裡的常客們,一聽說橘子下市就驚慌不已。「被紀州橘迷住的人們,真的好像上了癮。」布倫內斯笑著說。
世人大都認為,農夫種果樹是為了經濟高效大產出,而不是古董級別的異類美味。但心甘情願培育優質水果的人,往往很在意他們種的果實。最要緊的是有激情:水果說翻臉就翻臉,種好他們所需的技術和工藝是無止境的複雜難題。與此相比,把農場整個兒賣了倒更誘人些吧。當然,除非你真的是別無選擇才會那麼幹。
對澤布羅夫(Zebroff)一家而言,以土地為生意味著一家人全天候身體力行,包括兒子輩、孫子輩、侄子、外甥和別的親戚。「種地不簡單,但我們不覺得種地是工作,」喬治 ‧ 澤布羅夫說,「我們不是在這裡工作。我們住在這裡。」
2006 年 8 月,我造訪位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斯密卡曼山谷的澤布羅夫農場,在大門口迎接我的是女主人安娜。她就像成人版的長襪子皮皮。我們走進穀倉時,她理了理頭髮上的方巾,然後遞給我一杯加了一整勺蜂蜜的鮮牛奶。蜂蜜溶入剛擠出來的熱乎乎的牛奶,非常好喝,真是個好兆頭。喬治還在盛滿桃子醬的大鍋前幹活,於是,我們就在崎嶇不平的農場地裡信步悠遊。地上可熱鬧了,長滿了蔬菜、花朵、香草和果樹,每一寸地都沒閒著。他家的後院緊靠陡峭山壁,背風擋雨,形成完美的氣候小環境。母雞到處亂走,用安娜的話來說,他們是在給蘋果樹澆肥呢!「別的農場看似凡爾賽。我們這兒呢,樹邊都是雜草,我們都不去管,隨便長。我們的農場也是動物、植物和昆蟲共同生活的家園。」說話時,一只蒼蠅停落在她的眼簾上,一動不動地趴在那兒。她真是習慣和大自然渾然一體了,壓根兒沒注意到它。
喬治 ‧ 澤布羅夫忙完了果醬,走出來和我們會合。一開始他有點沉默,甚至感覺有點嚴肅。不加修剪的灰髮襯著鬍鬚,一副飽經風霜的模樣。他很高,和他握手就好像在和羅得島的太陽神握手。他帶著懷疑的神色打量我,又問了一遍我的書要寫什麼。經過一番言簡意賅、一針見血的盤問,他終於認可了我的寫作主題,轉而變得非常友好,出口成章,滔滔不絕。
他贊成伍德的論斷:買食物確實比種食物便宜,但人們曾經高度評價種植這件事。「現在,人們覺得農民就是胡搞瞎搞的爛人,只知道索討津貼。」他說,「在我們這行裡,有一條根深蒂固的底線。基於這個信條,企業模式完全可以預見。不正當的企業操作,都是有案可查的。在他們親手打造的世界裡,這就是生命線。」

我們吃他們自家種的葡萄,喬治看著一隻麻雀誤入藤蔓間的網。他輕輕地把小麻雀救出來,放飛空中。澤布羅夫一家和許多農夫不一樣,他們不殺任何行走江湖的動物。甚至,從山上爬下的蛇被困在藤蔓間,他們也會放生。他解釋說,他們承擔所有損失,而不是把損耗壓到最低並轉嫁到土地上。他們的目標是創建和諧家園,而不是賺大錢。為此,他們把許多植物種在一起。他們吃的是最好的,賣出去的也是最好的。
他當場邀請我吃。他抬頭看樹,想找出最好的青梅,這讓人頭暈眼花的,然後直接摘下來,我嘗了嘗,立刻就服了,這滋味美的,不服不行。能這樣活著真是福氣啊!他們種的桃子也好得不得了。令人心醉神迷的桑椹汁液豐沛,染紅了我的手指頭。「我們真正追求的是非標準化、非均一化的水果。」喬治細說道,「要論質量,就必須完整地看待他們各不相同的形狀、質感、口味等感官價值以及營養價值。沒有兩個水果是一模一樣的 —— 他們也不該如此。」
他們在不同年份種下不同種類的果樹,為了確保他們每年都能得到果實。「大多數的果樹,天生就是兩年生果。」他說,「他們不應該每年結果,所以我們任其自然生長。別人都強迫他們多結果。可他們也需要喘口氣。他們剛剛收工,你就必須等待。所以,多種幾樣果樹是有好處的。」
澤布羅夫的農場裡完全不用化學產品,他談起其他大型有機農場主時難掩輕蔑之意。他堅信「有機」首先關乎多樣性,而決非必須依賴噴霧澆水的單一作物農場。澤布羅夫一家很少買東西,除了農用設備、燃氣之類的必要用品。當然,他們也會買食物,但只限於他們種不出來的農產品。安娜承認自己隔一段日子就會忍不住去買香蕉,只因為在當地氣候條件下實在種不出香蕉。
澤布羅夫夫婦說,他們不知道是不是還有人像他們這樣生活,他們太忙了,沒時間去找同道之友。我問道,現代人是否依然能純粹靠土地生活?喬治回答:「當然可以。只要他們願意幹活。現代人幹得了嗎?當然能,可是他們得交一大筆學費才行。你看過《城市鄉巴佬》嗎?」
「比爾 ‧ 克里斯特(Billy Crystal)演的?」
「對!」他說,「你記得傑克 ‧ 帕蘭斯(Jack Palance)的那場戲嗎?他談起生命的祕密,說著說著,傑克 ‧ 帕蘭斯舉起一隻手指,說道:『祕密就在於只做一件事,只打一份工,專一而專營。』就是這句,你知道嗎?那不是祕密,只是文化灌輸。」後來,在我們的採訪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問他為什麼這種務農方式已然消失,澤布羅夫伸出一根筆直的手指,重申了一遍:「傑克 ‧ 帕蘭斯的手指!」
我們坐在野餐桌旁,吃著自家產的麵包、乳酪、番茄、紅辣椒和花園裡摘來的香料,我跟喬治說起我在溫哥華美術館看過的一次展覽。那是印第安海達族人的藝術回顧展,海達族是居住在不列顛哥倫比亞海岸線以西 60 公里的海島上的原住民。自古以來,他們把所有日用品 —— 獨木舟、衣服、器皿、木槳 —— 都雕刻成美麗的藝術品。我在美術館禮品店裡翻看畫冊時,碰巧看到一個海達人的語錄,至今難忘,彷彿深深鐫刻進了我的腦海。他說:「歡樂是精心打造的成果,只有創造時的歡樂才能與之媲美。」澤布羅夫正在給我們倒自家產的李子蜂蜜酒,聽罷此言不禁頻頻點頭:「他說的正是我們的信條。」
現在,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大規模生物滅絕的時代。為了得到木材、紙張或畜牧場,人們不斷砍伐雨林樹木,隨之而來的結果是,我們每年大約失去一萬七千五百種物種。有些物種從未被記載,卻永遠消失了。
不過,滅絕也是一種自然現象。99.9% 曾經存活過的生物物種,現在都滅絕了。他們幾乎都是在人類出現之前消失的。我們只能想像那些生物大概的模樣 —— 但我們也得慶幸,還留下這麼多豐富多彩的生物陪伴我們。
農民只能靠種植特定物種,來幫助維持生物多樣性。喬達諾農場的主人,大衛 ‧ 喬達諾(David Giordano)用他父親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用過的根莖培育新苗,從而挽救了莫派克杏(Moorpark apricot)。「你可以在別處得到莫派克杏,但那和我的杏子不一樣。」他對我說,「我保護他們。」儘管莫派克有點偏綠,味道卻是無敵的。「人們看到它的時候常會皺鼻子。」喬達諾說,「我給他們一顆嘗嘗,他們就都叫起來:『哎呀!我的上帝啊!』他們總是從懷疑到接受,然後就問:『我能買多少?』」
保護一種水果的最好方式莫過於創造需求,讓更多人嚮往它。畢竟,水果想被吃掉,以利繁衍。所有消費者要做的只是想吃他們。事實上,你認為許多水果日漸式微,但他們仍在一些小農場裡生機勃勃。肯特 ‧ 懷利(Kent Whealy)是品種保護交流會的創辦人之一,這個非營利組織旨在推廣對祖傳蔬果的復興。20 世紀 70 年代,他開始尋求星月西瓜(Moon and Stars watermelon)種子,這個特甜品種在 20 年代曾風靡一時。可惜,怎麼也找不到。坊間傳言這種西瓜已經絕種了。1980 年,密蘇里州梅肯鎮的農民梅爾 ‧ 范多倫(Merle van Doren)找到懷利,說他正在培育這個品種。現在,星月西瓜成了品種保護交流會裡最暢銷的祖傳水果,在無數人家的後院裡蓬勃繁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