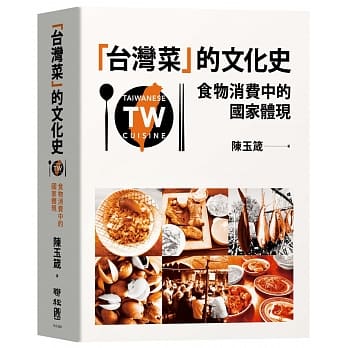1950、1960年代的台灣,在政治上處於戒嚴與思想箝制,文化上則強調中國的正統性,國樂、國劇、國語等以北京為典範、正統的文化建制工程積極進行,文藝寫作亦以發揚民族意識、反共抗俄為主要宗旨,故宮國寶、中國宮廷式的圓山大飯店等均被認為是能夠強化國民黨代表「中國」正當性的方式。在此脈絡下,烹飪與飲食作為中國文化與文明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也被視為宣揚「中華民國」正統性的重要途徑。而知名的烹飪教育家傅培梅(1931-2004),便是在此種政治局勢下將烹飪教學事業提升到外交的層次,她不僅是著作等身的食譜作家、第一位在電視教授烹飪的主持人,更被國家賦予發揚中華美食文化的重任,有「美食大使」之稱,這是傅培梅與1960、1970年代乃至今日的台灣其他食譜作家截然不同之處。
。.jpg)
傅培梅在七十多年的人生中出版了五十餘本食譜、涵蓋四千多道菜餚,她在1969年即已出版中英雙語《培梅食譜》,之後又再版二十餘次。而無論是食譜或電視節目,她的觀眾群都不限於台灣,遠至菲律賓、日本等地的華人社群,創下高收視率,還曾與日本食品業合作。藉由當時的新媒體─電視─及食譜的傳播,無論是本地台灣人或來自不同中國省分的觀眾,均有機會採借其中的菜色於家中餐桌上,更迅速地達成中國多省菜系的傳播、融合與在地化,藉由家庭餐桌上的多元融合,對台灣日常飲食產生深遠影響。綜上,她所具有的重要性至少可從三個面向來談:(一)烹飪教育;(二)「中華美食」的海外宣揚;(三)各省中國菜在台灣的融合與在地化。
除了傅培梅的影響之外,經由小食攤、市場、餐廳的不同管道,戰後二十年間各種中國菜餚已在台灣形塑出新的地圖(culinary map)與新的菜餚階層(culinary hierarchy),即是一移植到台灣的中華菜系,各菜系的地位高低與普及度則各有不同。這個以中華菜系為主體的菜餚地圖取代了日治中、後期受日本影響所建立的「漢(台)─和─洋」菜餚類型,而在這個以中華菜系為基準的新地圖上,「台灣菜」的新定義也逐漸確立,即是中華菜系中位置邊緣的一支,新的「台菜餐廳」於1970年代陸續出現,然而此時的「台菜餐廳」已與日治時期的「台灣料理酒樓」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其差異將在本節末統整說明。本節即從傅培梅的多元角色與在台灣菜餚發展上的重要性開始,並繼之討論1960年代後期至1970年代台菜餐廳的興起。
一、「中國菜」在傅培梅食譜中的再現
傅培梅於1931年出生於中國東北大連的一個富商家庭,父親是山東省福山縣人,在大連開設進口歐美食品的洋行。由於自1905至1945年間大連屬日本殖民地,因此傅培梅自六歲便進入大連的日本幼稚園,接受日本教育。二戰後1947年曾插班北京民大附中唸書,1949年與大嫂搭船到台灣投靠大哥。
傅培梅原本不太會做菜,是在台灣與山東同鄉程紹慶結婚且孩子們均上學後,為了烹調好吃的菜給先生與牌友吃,「在先生面前爭回一口氣」,才開始勤學廚藝。兩年間花費重金聘請餐廳名廚至家中指導,學成後便進一步開班授課。1961年先在台北和平東路自家開設烹飪班,她為烹飪班編製的教材後來在1965年出版為《傅培梅食譜》。1962年10月10日台灣第一家電視台「台灣電視公司」開播,傅培梅在「幸福家庭」節目的烹飪單元擔綱,展開39年之久的電視主廚生涯,是台灣目前歷時最久的烹飪節目主持人。傅培梅的電視節目不僅在台灣播出,在美國、日本、菲律賓也可以看到。傅培梅在食譜中稱,她出版中英對照食譜的目的,是讓所有海外華僑都能「重嚐祖國佳餚」。傅培梅也多次被政府派到海外僑界示範烹飪或進行烹飪教學,並獲教育部表彰其影響力。
然而,與今日眾多電視烹飪或美食節目主持人不同,傅培梅的崛起與種種成就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政治條件,她所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著名食譜作者、烹飪家,更適切的說法或許是:一名中華廚藝的教育者與宣傳者。在傅培梅影響力最大的1960、1970年代,正是國民黨政府與對岸共產黨政權互爭中國正統地位,並在國際上積極爭取盟友之時,中國傳統文化對居於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而言,具有重要的象徵性意義。傅培梅在各國僑界教授中國各省菜餚,扮演中華烹飪藝術教育者的角色,其重要性正在彰顯台灣就是中國正統文化之所在,這點在1969年傅培梅最早出版的《傅培梅食譜》中可明顯看出。
在《傅培梅食譜》的英文序言中稱,中國烹飪藝術可追溯至五千年前的伏羲氏,中國的兩大哲學─道家與儒家─都蘊含了許多烹飪與用餐禮儀。孔老夫子所稱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更是鼓勵著烹飪技藝的精進。相較於英文版序言從古代中國烹飪傳統來談,中文版序言則強調,國父孫中山在民生主義中提出「食」為民生四大需要之首,飲食作為民生的基礎,鞏固的基礎能帶來富強的國家。傅培梅食譜的序言與今日食譜顯然十分不同,從伏羲、孔夫子到孫中山,藉由眾多中國文化傳統裡的重要角色,建立了從古代中國到現代的連續性,而這些形象也正是傳統中國「文化傳說」(cultural tales)中的重要角色,並由此凸顯中國烹飪藝術的重要性。
在中國文化傳統連續性的基礎上,傅培梅的第一本食譜介紹了100道菜餚,且依照中國地理區域分類。換言之,這本食譜所代表的不是傅培梅個人的創作,而是再現了中國代表性的地方佳餚,她在書中依照如下四大菜系(大致是中國的東、南、西、北部)四個地理區域介紹中國菜:
- 東部菜:以上海為中心,含江蘇、浙江
- 南部菜:福建、廣東
- 西部菜:湖南、四川
- 北部菜:京菜為主
在介紹各地區菜餚之前,傅培梅均以包含台灣、蒙古等地的中國秋海棠地圖示意,讓人一望即知這些菜餚的源起地,說明正是不同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造就了各區域不同特色的菜餚。
中的地圖.jpg)
儘管食譜的主要功能是作為烹飪的指導,但食譜除了功能性的角色,也往往具有象徵與情感上的重要性,特別是當食譜承載了關於過往的回憶、涉及流離遷徙的族群時,此種在象徵上的重要性特別明顯。傅培梅的食譜即在中國歷史、地理連續性的基礎上,協助維持並強化了在台灣島上對「中國性」(Chinese-ness)的認知,也具體地傳承了中國各地的菜餚。
此種中國烹飪文化的連續性不僅是作者的自我宣稱,在當時的國際局勢下,美國作為台灣最重要的外援,也對此做了象徵性的背書。在傅培梅的中英雙語食譜中,為食譜寫序的作者即是前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1966-1974間派駐台北)的夫人(Dorothy McConaughy)。之所以由美國使節夫人作序,一方面因為馬康衛夫人自己是傅培梅烹飪班的學生,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這本食譜特殊的政治性。在書的前言中,馬康衛夫人讚譽傅培梅的廚藝如同藝術,並肯定她的食譜必定能「增進中美人民的友誼與雙方的利益」。該序言點出了,該本食譜不僅是烹調方法的指南,亦被賦予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就是當時中華民國與美國間友誼的象徵。
除了食譜之外,傅培梅在電視上的烹飪教學同樣也是先按照中國地區的順序來選擇菜餚,然而,由於許多菜餚的食材無法在台灣取得,加以廚藝傳授的過程原本就是動態的,往往會加入新的創意或在作法上有所改變。傅培梅在節目中或食譜上都經常提到,某道菜的主要食材若不易買到,可用常見的其他材料取代,味道也是不錯的。例如,「松鼠黃魚」這道菜原本是用大黃魚,但黃魚當時尚無法人工養殖,野生黃魚在台灣又非常昂貴,因此傅培梅在節目中稱,雖然江浙館子中是使用黃魚,但觀眾也可改用鮸魚或其他細長型魚類,食譜中則是建議可用草魚,無論鮸魚或草魚,均是台灣較常見且喜愛的魚類,使觀眾不會因此對烹飪該菜餚卻步,也把這道著名的江浙菜,改造為台式的口味。
因此,在這個將傳統中華名饌「移植」到台灣的過程中,所移植的並非所謂「正統」、「正宗」的菜餚,而是在食材上採借台灣本地食材,或針對台灣本地消費者進行口味上的調整,加上烹調手法上的微調或修改,一個更接近台灣環境與口味的菜餚於焉誕生,儘管菜名聽起來仍是傳統名菜,但內涵已然改變。儘管無法調查究竟有多少家庭的餐桌上曾經出現了傅培梅所傳授的菜餚,她的影響仍不可忽視。藉由食譜與電視,多種中華菜餚進入台灣家庭的餐桌,從餐廳師傅的手藝成為台灣家常版的餐食,促成多種中華菜系在台灣的融合與在地化。
然而,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這些台人家庭飯桌上的家常菜卻不被特別賦予「台灣菜」的名稱,相較於日治時期日本人將殖民地上的風味餐食稱作「台灣料理」,是為了與「日本料理」有明顯的區辨,此時期人們習以為常的家庭餐食,因為不再具備「殖民地料理」的標籤,沒有區辨的需要,加上各家庭有各自的喜好與餐食差異,故不再有命名以進行區辨的需要。這也說明了,菜餚類型的「命名」,正是一個基於「區辨」的需要而有的行為,當區辨的需要不存在,菜餚的「類型」便不再有意義。在殖民時期結束、大批中國多省軍民來到台灣後,「台灣料理」一詞已失去存在的脈絡,「台灣風味的地方菜餚」之概念,隨著政治情勢的變遷,其意義重新被轉化,被納為中華菜系下的一支。
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符號學的概念對於理解此種變化有很大幫助,如同他所提出,所有概念需放置在一個相對的架構上才有特定意義。「台灣料理」是一相對於日本料理、西洋料理的概念,而這個料理概念體系則是來自當時統治台灣的日本,但當政治與社會結構改變,「台灣料理」失卻其脈絡,取而代之的,是相對於「中國八大菜系」的「台菜」概念,從台灣料理到台菜,實則顯現的是一意義脈絡的轉變。
從另一角度可討論的是「菜餚類型」的概念,每一種類型儘管各自有其特色,但在界定這些類型時,重要的是其邊界(boundary),也就是與其他種菜餚類型的區分。例如,湘菜、川菜、泰國菜均以辣著稱,但三種菜餚的「辣」又有所不同,這些不同不僅構成彼此間的界線,也正凸顯三種菜餚類型的特色所在。因此,如本書首章即敘明,在討論「台灣菜」的意義時,要討論的不僅是「哪些菜餚、烹調方式為台灣菜的特色」,更重要的是這個菜餚類型是在何種社會條件下被界定而出。政治體制與統治者的改變,明顯影響到對台灣地位的認知,也連帶影響台灣地方文化所被認定的所屬體系與文化特徵。
由於政治結構的變動,「台灣料理」在戰後不再具有意義而逐漸從台灣外食市場消失,接下來影響「台灣菜」邊界之劃定的,則是市場行為者,也就是餐廳業者,基於商業市場劃分的實際需求,要與其他餐館有所區隔,標榜地方特色的台菜館也就成為市場上新的餐飲類型,與其他江浙菜、北方菜、川、湘、粵菜等餐館有所區別。換言之,「台菜」在戰後隨著多個中華菜系進入台灣與興盛,被納為中華菜系系譜上的一支,本地地方菜改以「台菜」之姿,在1960年代重新站上新的飲食版圖,也有了新的消費群、競爭者、定位與相關論述。
二、1960年代後新興的台菜餐廳
台菜作為中華菜系之一支,可從當時的菜餚分類看出。例如,1963年僑委會選拔中菜廚師到日本、哥倫比亞、義大利等國工作,此項選拔以地區菜餚為分類標準,結果共錄取102人,其中錄取最多的是北平菜55人,其次福建菜28人,廣東菜11人,台灣菜跟四川菜都僅有兩人。另外,設於1961年的味全家政補習班也有開設烹飪班,烹飪班分為六科,除了西菜與西點外,中菜包括:北平菜、廣東菜、四川菜、台灣菜。這些分類方式將台灣菜與其他主要中華菜系並列,台菜屬中華菜系之一支,正是在此種分類架構下,相應於北方餐館、廣東餐館、福建餐館等多省餐館,「台菜餐廳」也在1960年代應運而生,且在1970年代更為蓬勃。
在1960、1970年代,標榜「台菜」為主的餐廳,有兩種不同的經營型態:
- 沿襲日治時期的酒樓文化
部分標榜台菜的餐廳空間大、可舉辦宴席,同時有唱歌、魔術、電子琴等表演節目。此種餐廳與日治時期的大型酒樓類似,均為能夠宴客兼舉辦娛樂活動的場所,不過娛樂活動從日治時期的藝妲表演、吟詩,轉變為歌舞或雜技演出,部分餐廳的演唱歌曲仍保有台語或日語歌曲演唱的節目。
在菜餚方面,由於此種餐廳多為舉辦宴席或應酬的場所,菜餚較為精緻,如日月明蝦、蛋黃石榴等菜餚,不僅食材較為昂貴,也較注重擺盤的樣式,有的甚至會排成山水畫或動物的圖案。由於當時許多餐廳的師傅都是來自日治時期的酒樓,日治時期的菜餚也有部分在這些餐廳保存下來,這些菜餚加上台語歌、日語歌等表演節目,呈現出與其他江浙館子、北方館子十分不同的用餐氛圍。
然而,此種型態的台菜餐廳在1980年代之後逐漸消失,消失的可能原因為,此時的台灣正經歷從農業轉變為工商業社會的過程,所得逐漸提升,外食人口增加,消費者需要更快的服務速度、更多樣化的菜餚,亦促使餐廳必須改變作法,過去費時耗工的酒樓菜色已不再符合商業需求。另外,因為此種菜餚在烹煮與擺盤上均過於費工,在教育制度變遷、有更多教育與工作選擇的情形下,願意學習此類手工菜的學徒也漸少。
- 清粥小菜
第二種型態的台菜餐廳在1960年代誕生,是當代常見「台菜餐廳」的源起。最初提供簡單的家常菜,包括台灣人日常吃的稀飯、簡單配菜,如菜脯蛋、煎魚,但也能提供食材較好的宴客菜如紅燒赤鯮、豬肝等。相對於日治時期的「台灣料理」酒樓大多為仕紳階層才能消費,僅山水亭等少數餐廳會供應台人家常菜餚,此時期的台菜餐廳可說是台灣庶民日常食物大量進入餐廳之始(關於台人日常食物請參見第三章)。值得注意的是,此階段的「台菜」雖以台人日常食物為主,但經過戰後十幾年新移民引入豐富中華菜系的影響,一般台人家中的菜餚或烹飪方式已有變化,也與日治時期的庶民食物有所不同。
此種餐館設備簡單,亦無表演,但仍可作為朋友小酌、小型宴客的場所。雖曰是「小型宴客」,但在1960年代,絕大多數台灣家庭均是自行烹煮三餐,除了工作所需的應酬之外,一般人僅有壽宴及婚喪喜慶時機才會外食,因此即使這些餐廳未必有華美的裝潢,「在外請客吃飯」已充分顯示出主人的慎重,也在能力範圍內準備合宜的可口菜餚。而在沒有宴席的時候,這些餐館也可以提供簡單的家常飯菜,即為日後人們所熟悉的「清粥小菜」餐館。
在此類型的台菜餐館中,目前仍營業者以「青葉」年代最久,自1964年營業至今。青葉甫在中山北路六條通開業時即在招牌上標示,其供應的是「台灣料理、清粥小菜」,主要開業者沈雲英女士曾在1970年的訪談中表示,最初是有不少華僑抱怨吃太多全席大菜,想換清淡的口味,她因此決定以稀飯、小菜為主,提供人們在宴客菜之外的另一種選擇。而對於什麼叫「台灣菜」,經常也是參考客人的意見,加入不少新作法。當時受歡迎的菜色包括醬油煎魚、滷肉、三杯雞、蔭豉蚵等,這些也是同時期餐廳中較受歡迎的台菜。青葉不僅是餐廳,之後也成立食品公司,著名歌仔戲演員楊麗花便是青葉的股東,經常作為青葉食品廣告的主角。除了華僑外,日本遊客也是此類型台菜餐廳的主要消費者之一,這點延續至今。
然而,與刻板印象不同的是,當時供應清粥小菜的,不僅是酒店或「台菜餐廳」而已,在1960年代後期至1970年代,很多餐館不論是供應江浙菜、義大利菜,或其他西餐,都會設置宵夜時段,供應清粥小菜,包括地瓜稀飯、菜脯蛋、蛋黃肉、煎虱目魚等,當時這些家常菜餚、稀飯、各種小菜便是普遍認知的「台菜」。有的餐廳除清粥小菜之外,也會根據餐廳屬性販賣其他餐食,例如,高雄市愛河邊的一家義大利餐廳平時主打紐西蘭牛排、義大利快餐、半雞等,「燭光宵夜」時段則改賣清粥小菜、酸菜肉絲、雞絲、餛飩等麵點,以及八寶飯、奶油雞餃、咖哩牛肉水餃等。台北的北平厚德福餐廳也在宵夜時段備有清粥小菜及各式原汁涮火鍋。另如賣湘菜的芷園餐廳、有歌星駐唱的珍珠坊餐廳等,都供應宵夜時段的清粥小菜,可見當時宵夜市場之大,餐飲業者無論主業為何,都想分一杯羹。
餐飲業的發展與社會變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清粥小菜餐館的興起也有其原因。1960年代,「夜總會」在都市裡興起,成為新的商業應酬場所。在夜生活愈益絢麗之際,也有許多酒店供應清粥小菜作為宵夜,同時間還有歌唱表演,有的餐廳在晚餐之後甚至有十二點以後的「宵夜」與凌晨的「小宵夜」時段,可見當時伴隨台灣貿易與經濟成長的,還有通宵達旦的都市夜生活。
宵夜與午、晚餐的差別之處不僅在營業時間及菜色,消費者亦有所差異。不同於午、晚餐為一般用餐時段,宵夜時段的消費者為半夜仍在外未歸者,除了在深夜仍須工作者如需輪班的各種工作者、計程車司機、部分媒體從業人員等外,更多的是在夜總會、舞廳等深夜營業場所工作的男女與應酬的生意人。整體來說,這些宵夜時段的消費者在當時輿論中常被視為社會地位較低的階層。如經濟日報記者宋梅冬在一篇〈如何開設中餐廳〉的分析報導中談到兼營宵夜場的利弊,就認為「宵夜食客良莠不齊,酒後易生事端」,且「宵夜毛利雖然較高,但呆帳比例也很高」。
特別是在1960、1970年代,這些新建的台菜餐廳,多位在中山北路與林森南路一帶,此區域當時亦是許多酒家、舞廳的所在地。宵夜餐廳的興起一方面顯示出工商業活動熱絡下夜生活的熱鬧,也建立了台菜與「宵夜菜」的緊密連結,彷彿「台菜」的內涵僅有清粥小菜式的宵夜菜。此外,由於台菜宵夜的消費者多被認為是社會的較低階層,也連帶促使台菜在中華菜系階層中被置於較低的位置。如前段提到宋梅冬一文指出,浙寧菜與川菜館是最受歡迎的中餐廳,因為這二種菜系「品質新鮮、口味清淡、海鮮多、脂肪少、菜式種類變化多」,且又以浙寧菜氣焰最盛。相較之下,台菜則「均為小盤式,較難登大雅之堂」。1977年開設台菜餐廳的一位老闆就提到,當初開台菜餐廳,有朋友笑他台菜只不過是路邊攤的小菜,還不如去吃浙江菜,讓他心中十分氣憤。

由前述可看出,即使均是中華菜系,其中仍有階層高低的分別,即「菜餚階層」(culinary hierarchy),某些區域的菜餚會被認為具有較高的經濟或文化價值,某些則較低,然此種階層亦會隨社經條件的變動而有所變化。在台灣的中華菜系也有其階層,且各菜系的階層高低仍會隨社會條件而改變。在1960、1970年代的台灣,中餐廳以江浙菜、廣東菜常被認為居於這菜系階層的頂端,另外川湘菜與北方菜也頗受歡迎,其他菜系則餐館較少也較不顯著。
綜言之,1960年代的台菜有兩個主要根源。一是延續自日治時期酒樓的菜餚,多是由原本在酒樓工作的廚師與其學徒們所傳承,如北投或大稻埕等原本的酒樓集中地,仍有部分餐廳提供此類菜餚,但隨著新菜系進入、消費者口味改變、技術傳承困難等因素,戰後二十年間已逐漸凋零。與過去酒樓的消費文化相較,此類餐廳仍有表演節目,但已從樂器演奏、歌唱、唱戲等表演型態轉變為納入魔術、歌舞等。第二個台菜的根源,則是從家常餐桌進入餐廳的「清粥小菜」系列餐館。此類餐廳供應的菜餚多為家常菜,也有部分是食材較好、可供宴席的菜餚,此類餐廳日後逐漸壯大為今日台菜餐廳的主要類型之一,但因第一種類型餐廳的消失,也讓大多數人遺忘了台灣曾有的酒樓宴席菜。
上述發展也影響了今日人們對台菜的認知、定位與述說方式。曾在日治時期酒樓或前述第一類型餐廳工作過的廚師,會強調台菜也是十分精緻、費工的「手工菜」,衍生出日後「台菜是酒家菜」這樣的說法。相對於此,另一群從清粥小菜餐廳起家的師傅,則傾向認為台菜就是宵夜菜、家常菜,由此也可看出,不同的工作經歷、社會脈絡,讓即使是台菜的圈內人(insider)、生產者,對於台菜的定義也有不同的見解與認識。而在1980年代後,隨著第一種類型台菜餐廳的消失,清粥小菜台菜館因為符合大多數台灣人的生活經驗,逐漸被認為是「台菜」的主流。直到2000年前後,新的社經條件下又醞釀出多元的新類型台菜館,如主打地方口味與食材、強調精緻化的台菜,或「復古」台菜等,當代台菜又已有一番新風景。
延伸閱讀: